IAAC 6 征稿
第六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现正面向全球公开征稿,稿件内容为针对当代艺术展览的艺术评论,投稿时间截止至2019年9月15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参与到艺术批评的写作中,征稿期间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将陆续邀请艺术界拥有不同身份、教育背景、实践经验的嘉宾展开艺术批评的系列活动。
编者按 | 在IAAC 6的征稿之际,我们在向前看的同时也不禁要反思当下艺术批评的境况,当艺术家也开始介入艺术批评的时候,批评家这一独立身份的意义该走向何处?艺术批评者面临艺术家的介入,将如何保有评论的专业性、独特性和客观性?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关系又该走向何处?
为此,我们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共同邀请了多位艺术家与艺术评论人、策展人同台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激发对艺术评论、艺术创作等艺术各个领域更多维的讨论与思考。
艺术家真的需要批评家吗?

邵亦杨
中央美术学院(CAFA)人文学院副院长
当代艺术到底走向何处,艺术理论到
底走向何处,艺术批评还有没有作用?
我在2008年写过文章说“艺术批评死亡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我觉得艺术批评现在面临着很多危机。一个是话语权争夺和难以保持独立性的危机,这个时代批评家可能成为商业宣传者,或成为政治宣传者,很难有独立的立场。
而跨界现象的加增与社会政治性语言的介入也导致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的走向渐渐模糊,甚至一度被赋予消极的评判。2000年以后丹托的哲学思想就判定艺术已经死亡了,艺术批评也不行了,将它们都归入了哲学。所以我们现在再谈艺术批评,好像是个老旧的话题,但其实艺术批评一直都在。近日,大家又开始对艺术批评进行反思,我不禁想问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到底走向何处,艺术理论到底走向何处,艺术批评还有没有作用?这在当下又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80年代的中国,或者更早一点的美国,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能够直接推动艺术运动的发展。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时期到来以后,艺术家不再是有特权的天才,大家的视野都开阔了。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都加入到艺术批评的行列来,批评家、艺术史家他们也吸收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包括科学和哲学。所以它也不再局限于几个艺术家或者艺术运动。那么,这种语境下的艺术批评应该怎么做呢?

高名潞
当代艺术理论家
策展人
不要让这些概念困扰我们,
例如艺术的终结、历史的终结、
批评的死亡等等,而应该仔细想想我们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艺术家和批评家各自的责任。
我觉得艺术有没有危机,批评有没有危机,历史是不是终结了,这些问题都是造出来的,都是现在理论家自己喊出来的,我倒觉得不一定有这么回事。就像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每个阶段的关系不一样。非得让批评家和艺术家绑在一起,就像婚姻关系似的,这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处于一个自然状态。
今天说“艺术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批评的死亡”,这类概念在70年代的西方大量出现。完全没有必要被这些概念困扰,更重要的是仔细地想一想现在的状况,我们面对的现实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艺术家要搞创作就要想一想自己能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更进一步在原创性的基础上还能有一定的共识性,而且这种原创性是可以延续的,可以有发展空间的。批评家进行评论写作首先得老老实实做点学理上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哪个作品、艺术家或者展览真正触动你,令你不得不发声,这个时候你再有感而发地去评论,我认为这就是批评家的责任。
如果大家都是这么去做的话,就没有什么危机、死亡,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在各个阶段尽到责任。
不要被现代分工所赋予的身份束缚
而艺术家、批评家这样的划分是现代人划分出来的,对于中国古人、古代来说,没有批评家和艺术家、画家的概念。因为中国最的早文、书、图的概念,它都是互相相互存在的。董其昌是批评家还是画家?苏轼也可以是批评家,所以这个分工是现代以来受到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分工。分工本身是有好处的,每个领域可以做得更细致一些,但是这也容易走进一个窄胡同。
批评家既需要和艺术家来往、
交流,也需要静下心坐冷板凳。
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也一直关心批评的问题,但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最主要的事情。90年底我离开国内,开始更多关注一些西方的现代性和前卫艺术等等问题,这些都是我自己从中国带过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梳理西方的理论,后来把它写出来。我想告诉中国的一些读者、艺术家、批评家我所感觉到的东西。但是我跟艺术家之间是若即若离的,回来了我一定要考察艺术家,一定要跟他们交流,但是我回去以后就得坐到冷板凳,我就得去读书,就得去研究写作。
自从新世纪以来,我两边来回跑,教学,还同时在做研究写作,所以我对目前中国当代现代批评现状还真是不太了解,我也没有太多的批评文章。但是去年我参加了评选,参加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活动,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都是年轻的写手写作者,我很愿意跟他们进行交流,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写作,在关心些什么。所以虽然这个奖项是国际性的,但我倒觉得年轻人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那么神秘,也许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因为像格林伯格那个时代那样的批评家早就已经没有了。哪怕在国外也没有谁是顶级大批评家,站那儿一呼百应。而且真正有影响的批评家更多是从其他领域跨界做的批评家。
去年的评奖中,很多年轻人或许会因为这个奖项的国际性,所以选的题材就国际一些。我觉得做艺术评论不要去迎合,而要去表达你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哪怕是就在你身边举办的一个国内的、小型的展览。这样才更能够建设我们自己的批评。
关于批评的很多问题中,我更愿意强调实践问题。现在正是年轻人抛开各种各样现成的成熟教条,做出独立思考的时刻。因为世界很复杂,艺术现在面临的问题也不只是艺术,所以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

隋建国
艺术创作更像是一个生产过程,
与批评家、策展人产生关联是在“孩子”出生之后,而生产时的痛苦与狂喜是他者难以感同身受的部分。如同批评家享受写作时独立思考的过程。
作为一个艺术家,做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状态,是自己享受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就像大家都读过的米开朗基罗传记《痛苦与狂喜》,当创作遇到坎儿的时候你觉得痛苦,完成了之后是狂喜,这痛苦与狂喜只有你自己能够享受。我想,这就是艺术家没法让渡出去的哪一部分。
不管是批评家还是理论家,还是艺术史家,他跟艺术家的关系是创作之后的关系,就是你生“孩子”生完了,这个“孩子”要拿出来了,这时候批评家、理论家、艺术史家就开始起作用了。有意思的是这个“孩子”的好坏,可能批评家、理论家、史学家有发表观点的权利,但是艺术家自己的痛苦与狂喜是很难与他们分享的。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要独立思考,批评家、理论家和艺术史家他们享受的是他们独立思考的过程。当然,他们也会享受与艺术家交流的过程。作为艺术家来说,我的立场大概是这样的。
没有批评家的艺术界是不完整的
从80年代到2000年前,中国的当代艺术是非常热门,大概一直到2007年、2008年之间都是这样。在艺术市场出现之前,批评家、理论家的发言权还是挺大的,但这些年好像有点沉寂。所以我也很好奇,我们50后这一代人和现在正活跃在艺术阵地上的年轻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们的相同点在哪儿?不同点又在哪儿?于是我会跟画廊老板说,光出钱策划展览不行,你还得出钱请策展人、批评家来讨论这个展览和作品的定位,这样才是完整的。
在陈旧的理念中,很多艺术家基本上是一个疯狂的人,特别偏激,闷在屋里不出来甚至恨不得不跟人交流。在那个时候,批评家和理论家对其作品的阐释作用就更为重要。如果遇到格林伯格这样的人,他们甚至直接给你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就成为一种潮流,甚至很多艺术家都可以赶这个潮流。其实美国古典主义时代好多艺术家就是这个潮流,今天卖了上亿人民币,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话说回来,说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眼下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确实存在好多限制。所以我时常鼓励自己的学生、鼓励艺术家,“其实我们那个时代也许好东西都做出来了,不过是还没有人把它写出来而已”,也算是抱团取暖吧。

邱志杰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亦敌亦友。
首先,“艺术家需要批评家吗”这个问题没法直接给出答案,因为艺术家有很多类型,批评家也有很多类型。有的艺术家很需要批评家,比如我,而有的艺术家根本不想听别人的意见,自己构建标准,自己搞定。另一方面呢,有的批评家讲的话是值得听的,而有的批评家讲的话不值得一听。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
就拿我来说,我会很在意高士明对我的评论,但有一些评论我一点都不care,这才是艺术家跟批评家的真实关系。某些人对我的批评总是能给我开脑洞,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样的批评我会很在意,甚至会让我觉得这种“遭遇”很幸运。所以我觉得没办法来泛泛地说今天艺术家是否还需要评论家。
艺术家需要真正的批评家而非阐释者
其实我们经常把“批评”跟“阐释”混为一谈,很多人自称批评家,他们往往只是对作品进行阐释。阐释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作品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换作古典时代,他就在扮演艺术家的肢体,他跳出来说这个作品是这个意思。艺术家一般会说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而这类阐释者相信,我的这个阐释虽然不是你心里的那个东西,但起码是一千个哈姆雷特之一吧,我有发言权。还有一类阐释者把自己当心理医生,他说你“其实是什么”,艺术家自己都不知道,我比你更知道你自己,你的意思其实是这个。
所以这是一套关于阐释的艺术写作,而我理想中的批评,是直接对作品的优缺点进行评判,去回答这个东西好不好;以及,如果不好,不好在哪里?在回答好不好之余,甚至于能够提出假如你要做得好应该怎么做好,能够提出建议,这是我特别渴望得到的批评。
好的批评家如同一位诚恳的友人,能够促使好的艺术家不断进步。
真正强悍的阐释者,他们其实根本都不需要艺术家,也不需要艺术家的作品,给他一块砖头,他就可以进行淋漓尽致的阐释了。他们能够把稻草说成黄金,把乌鸦说成天鹅,但是这样的阐释者我们艺术家真的不需要。我需要有一个诚恳的朋友来告诉我我所看不到的那一面,因为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他是会去修改他的作品的,他不会这个作品做完了就放在那里,那样的艺术家是不会进步的。一个不断进步的艺术家总是在听到某种意见之后转身回到工作室去埋头苦干,这次没搞定,哪里不对了,哥们儿告诉我,我回去修改我的作品,这样的艺术家会越来越好,会成为真正的好艺术家。
敢于提出和讨论多元的标准和观点,才能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有所进益。
一个人拿着自己的标准去要求艺术家,去对艺术家提出评判,是一件很霸道的事情。但是正因为人人都这么做,我们才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漫无边际地进行阐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哈姆雷特,这样的东西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两者本身都没有帮助。既无助于我们通过论辩走向真理,也无助于我们通过论辩最后达成共识或者形成求同存异的局面。而当每个人都拿出他的标准,接受这种多元,在标准和标准之间又保有协商的余地。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多元的观点和标准最后慢慢地可能会凝聚成一种共同的东西。
第二个,身份问题其实也不重要。黄庭坚写在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的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这一段话也应视作一段批评。但是黄庭坚自己也是一个大书法家,这是一个身份的切换。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共同体中,谁是策展人、谁是批评家、谁是艺术家,或者谁是美术史家,这个身份的切换是非常有机的,需要视情况而定。所以没必要非用这套分工体系来切分身份,就像我也会很积极的去写作一样。
好的艺术批评需要好的制度保障
现在批评的问题,其实是我大概在15年前、20年前意识到一个问题,中国批评的问题,我倒不觉得是高老师说大家独立性不够,大家人格都挺牛的(笑),都很高洁,而且不能用道德水平要求批评家要人格独立才能写出好的批评。我说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批评家的稿费太低,而稿费太低不会有好的批评。当一个一流的批评家开着一个QQ,三流的画家开着一个奔驰的时候,怎么会有好的批评。所以稿费的高低是一个关键,而且稿费得由独立于画廊和艺术家的媒体来发。如果画廊买单,艺术家买单,那就很难有好批评了。毕竟拿了别人钱还写文章骂人这样彪悍的人格在中国罕有,所以我觉得提高稿费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我们的媒体能够支付批评家写作的稿费,让他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收入,那么批评自然就好起来了,人格自然就独立了,学术水平自然就变高了,这是我的解决方案。

田霏宇
UCCA馆长
艺术评论的最大作用
在于为这个全民可以参与
评论的时代提供评判标准的引导。
批评家还有这个问题,他们会看得比所有人都多,所以这种专业的观展经验不能做为大多数人的阅读背景。所以我认为,艺术评论最大的作用并不是直接决定作品的好坏,或者决定未来的风格走向,而是为大众共同话语的构建起一个疏导的作用。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提供了多渠道的发言平台,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意见和感悟,都可以参与艺术评论。但是,最后总有一些人在引导整个评判标准的方向,哪怕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构的时代,我们的价值标准和走向总是会有一个方向,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是相对有价值或者相对缺乏价值的。而艺术评论的最大作用就在这里。
同时,这个价值肯定是跟我们的时代、我们所在的地域的价值观是相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的特别之处,这些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参选文章统统经过翻译后进行评审,获奖者可能是中国作者,也可能是外国作者,这一点是无法预知的。而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这样的交流非常有意义,这也是做国际奖项的意义所在。
身份的切换其实只是表达方式的切换
所谓的身份切换其实是一种表达方式的转换,因为策展也是一种写作,只不过运用了不同的媒介和形式,但最后其实都是跟评论有关,都是跟修辞有关,目的都是要传达一个观念,或者提出问题。所以不需要把评论局限于“写”这一种渠道。
警惕教条性的趣味
另一方面,评论家的影响力过大也是很危险的。我近几年接触了一些做葡萄酒评论的人,发现葡萄酒界特别像70年代的艺术界,有一位美国葡萄酒评论家叫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er),被他评高分的葡萄酒价格不菲。而且这个人的影响力近似于格林伯格,他的出现和他的评判系统的普及,逼着大量的酒商开始产一些大酒精、大糖分的酒,所以这样的酒在90年代盛行。回到艺术界,90年代的艺术全球化也产生了很多这样的教条性趣味,而近些年才开始解构。一个评论家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仔细一想是蛮可怕的。
而作为策展人,我不指望对艺术家起什么直接作用,我们肯定是走在艺术的后面,要么在梳理,要么是在呈现,是在为它服务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把艺术的魅力结合更深层的思考配合空间的展陈展示给大众。或许艺术仍旧是少数人能够进入的领域,但就像T台时装,可能没有人穿这些衣服,但是它会影响到各个小店铺中正在售卖的东西。所以,所有人都依然要参与艺术这个话题,要相信它,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策展、批评或创作都可以。同时,也要记得这不只是为了拿到什么样的成绩,而是为了对艺术能有更多元、更丰富的认识。

高鹏
今日美术馆馆长
提到价值观的问题,虽然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现在批评的环境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在今天去提“批评”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在很多环境下,其实很多的问题是不能够去碰及的,即便你批评了,你也没有办法将其呈现给公众。当你很多问题不能提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只能提钱,这点很现实,但是也确实无奈。而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就已经被裹挟掉了,如果坚守一个严肃的独立人格去批评,很容易落得没有渠道发声的下场。
我一直保持很严肃的态度去思考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去看西方的批评会发现,西方和我们的价值观确实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的。比如西方大量价值观源于《圣经》,而我们源于我们的老庄。中国讲求诗意的内部感受,而这种诗意要是按照西方的批评理论去写,放到西方语境下去进行评论,我们会发现这是很别扭的,甚至会有一点手足无措。
当我们对这个生态不了解的时候,无论是批评还是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变得非常的突兀。
还有一点是整个艺术行业的生态问题,在学生时代没有很好的了解到这个生态环境,导致了一个二元的认识局限:要么去做批评;要么做一个艺术家。但是,其实无论我们如何跨界,无论在哪个环节、哪个职位,首先我们都要遵循这个行业的生态所要求我们要尽到的职责,再去做跨界,去做另外一件事。整个艺术生态中的元素有博物馆、美术馆;有画廊;有博览会、拍卖;有艺术批评、艺术史家;还有最重要的艺术家。首先要建立一个宏观的生态意识,建立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目标就是让这个生态链越来越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坚守独立人格,无论是指责还是赞同,大家的目标都是统一的,都是为了一个价值观统一的生态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当我们对这个生态不了解的时候,无论是批评还是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变得非常的突兀,每一个环节都是散乱的。最后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无法建立一个有机联系的价值观和生态链。
每个人都可以去批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这个时候批评的标准和价值就变得尤为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渠道,80年代我们对批评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的媒体非常局限,好的批评家就那么几个,好的杂志就那么几本,只要文章一发表,基本上全国的很多艺术界人士都可以看到。但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这个媒体爆炸和改革的时代,获取信息和发言的渠道都被打开。每个人都可以去批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这个时候批评的标准和价值就变得尤为重要。现今杂志的权威性大大削弱,导致读者不再那么认真地对待那些杂志和其刊登的评论文章,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重新摸索和重建
价值观的时代需要问题意识
最后,我觉得这跟年龄没有关系,而在于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新摸索和重建价值观的时代,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反思这件事情,艺术批评也会重新启动。我相信只要你对这个社会、对现实有观察,往往就会发现问题,只要有问题,你就能表达,你只要有表达,你可以成为艺术家,你也可以成为批评家,当然也可以成为艺术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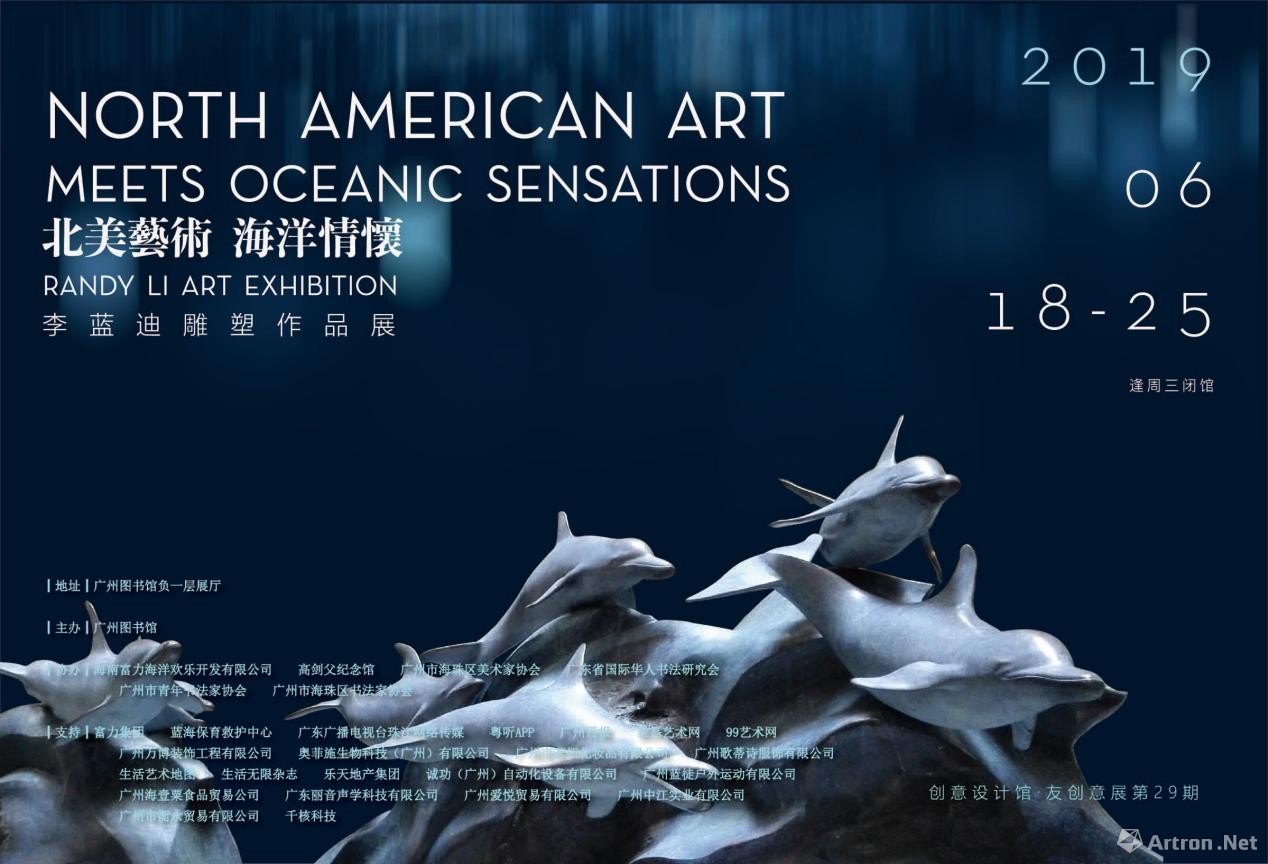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