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明安·赫斯特与作品《看在上帝份上》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导师Jonathan Miles在《现代性的确立:可见与可诉》系列课程第十四讲,梳理了科技美学的历史。迈尔斯认为,使用各式各样的科技:公关手段、虚拟科技、工业技术、广告策略与宣传手段等的科技美学是经济变迁的产物、属于领域间的转变。作为新的艺术工具,不仅改变作品的展示规模大小,使其成为商品和生产线上的产品;它也是艺术生产方式转换的主要驱动力,符合经济合理性。
达明安·赫斯特的“闪亮美学”一尘不染,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于科技准则与美学准则之间如何融合的思考。Jonathan Miles给出的回答是,通过领域变换而实现,正如1979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条件》中所言:“世界上各种知识如何开始突变是开端。
科技美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又叫科技未来主义。科技变革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艺术家把关注点聚焦在未来。这一阶段的社会背景是俄国革命,它不仅是新社会制度的开拓,还开启了工程师与艺术家之间,属于构建者和制作者相互融合的新领域,艺术家利用新科技来塑造一个新的社会形象。代表性的艺术家有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和他1919年的著名作品《第三国际纪念碑》,是俄国革命与美学相融合的产物,兼具实用价值和未来性;还有埃尔·利西茨基在1924年创作的《构建者——自画像》以及亚历山大·罗德琴科等等。
其中也不乏对工业主义的乐观主义,以弗利茨·朗的《大都市》反科技式的反乌托邦,思考人与机器人置换;以及摄影师莱尼·里芬斯坦尔在1937年拍摄的《意志的胜利》,记录法西斯的政治美学,同时揭示权利气息下奇怪的形式美。关于法西斯的思考还有艾伯特·斯皮尔重新设计第三帝国的现代建筑,法西斯作为符号介于美学、政治、科技和艺术之间。
随着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具有前卫意识的威廉·德·库宁提出“原子弹将带来新的认识并将彻底改变绘画”。随后艺术家开始对现代科技反思,戈达尔在1965年的《阿尔法城》便揭示了反乌托邦式的科技对人类社会未来冲击的猜想;还有居伊·德博1967年的《景观社会》表达对科技社会的恐惧;有同样觉醒的艺术家还有雷德利·斯科特、常·德里罗以及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等。
以上激发了科技美学的第二阶段,艺术成为景观。从新兴大型博物馆的场馆设计理念到经典美术馆馆藏的收纳,新的博物馆空间逐渐收藏科技美学作品。成功把艺术品制作成为超级商品的杰夫·昆斯、村上隆和达明安·赫斯特,背后都有庞大的高科技建构团队。近年来很多科技美学作品陆续出现在各大当代艺术展览,并广受好评。
Jean Baudrillard说:“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there is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and less and less meaning.在这个信息过度、图像泛滥成灾的社会,既然科技美学已成趋势,那么艺术是否会消亡?是否会被信息时代取代?是我们应该慎重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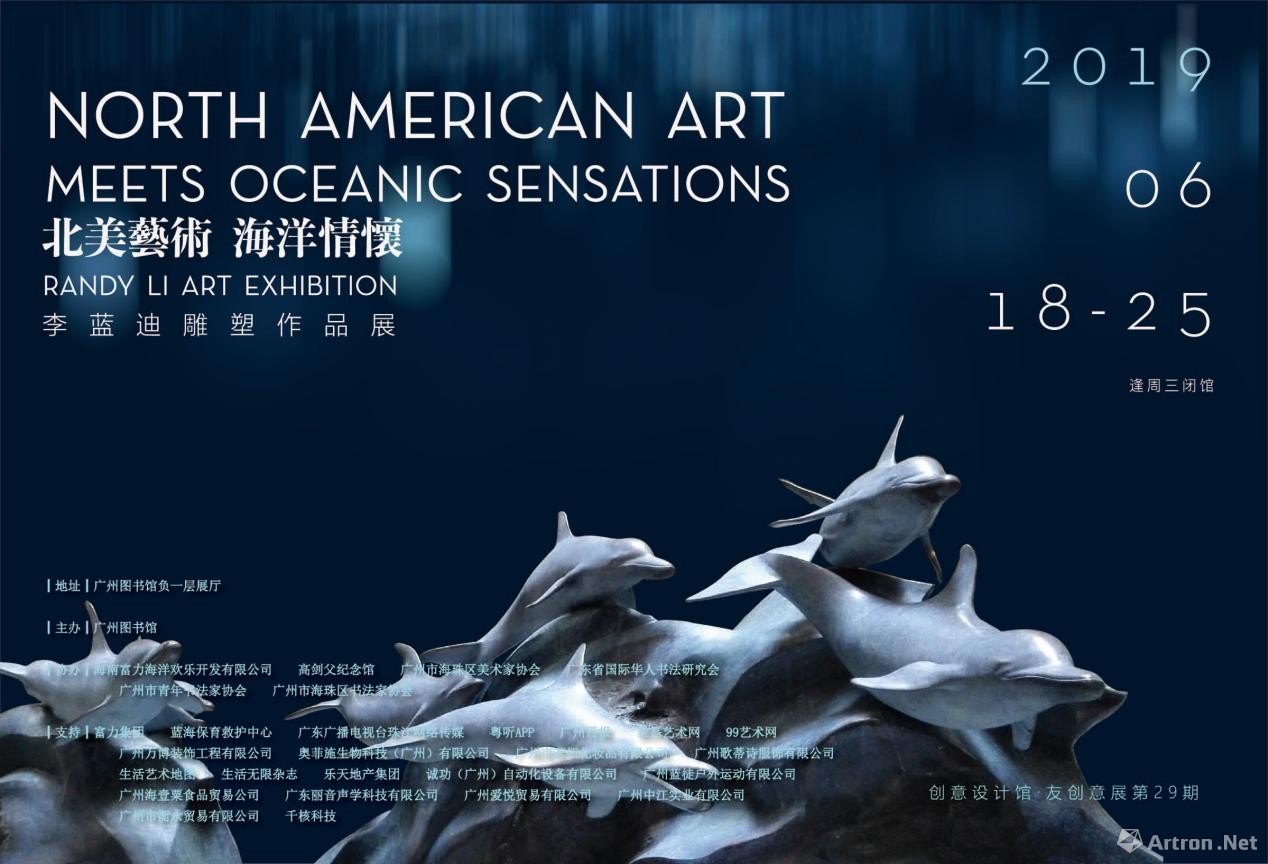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