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里的教学范式
Q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课程被转移至线上,您的《建筑基础与构造营建》课程也需要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开展,您认为这种授课形式包含了哪些挑战?
苏丹:
挑战在于你要克服过去的习惯,这个习惯是指你的思维和身体感知形成的一个系统,过去我们站在讲台上,站在学生身边,如今这种形式没了, 但是对知识的整理不受影响,甚至知识的呈现还会更清晰一些,这可能是它的一个优点。确实还是存在挑战,很多老师讲完以后都会反映,一上午讲下来筋疲力尽,而且你对着屏幕说话的时候会感到口干舌燥,这个我认为是身体的陌生感所引起的一种神经系统的变化,这也是挺值得研究的一个事。
线上授课它有多大的优势?我认为它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们也期待将来在技术上会有更完善的进步。我从1988年开始教学到现在,30多年来形成了教学方式,对很多职业教师来讲,(传统授课)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当你对着一个没有互动的屏幕在说话的时候,人整个的肢体和神经系统反应很不一样,就像龟在陆地上爬得很慢,爬不了多远,但是在海里却能游几千公里一样,因为它用力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设计课程还是以辅导为主,辅导课程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它会存在很多的空隙。比如,你可以闲下来走几步去调整情绪,然后再说;但到了网上,这种空间就消失了,全部被压缩到一个无法逃避的扁平空间里,一步接一步一直在走,这也是我认为这是网络授课相比于传统授课使人更疲惫的原因, 它其实是把密度增加了,把空隙都压缩掉了。

项目工程照片-日照科技馆
Q
环境艺术作为一个对空间体量极为敏感的设计学科,您是如何在无实体的网络界面中向学生传授这种需要真实感知,较为隐性的专业知识的?
苏丹:
有些东西必须是实体授课,我觉得精英式的教育如果消除了实体空间与对现场的认知,那就不算是精英教育。像最早的电视广播大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说明它(远程授课)不是一个新事物。但知识的传播一定是有它的特殊性与偶然性的,针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讲出的话也一定有所区别,这是我觉得教育里最生动的东西,网课是替代不了的。
我本次所上的课知识性比较强,所以受到的影响还比较小。假如说我真要带一门设计的课,带一门和环境现场认知相关的课,比如教《中国古代建筑史》,要去认知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你要去认知这段历史,你不到现场是不行的。过去没有条件,大家就靠课本,教师就靠板书。后来有了幻灯片,有了投影,但是那种对场所的感知在精英教育里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常常听说美国学生学欧洲的历史,要去站在罗马的废墟上,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这很奢侈,但是没有意识到它多么的重要。后来,我们亲自到了现场后,觉得对历史的想象,书本和文字上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 人必须要站在一个现实的空间里面,这是网络授课所无法替代的。
还有就是像空间营造这种课程,它在知识过于系统化之后,实践慢慢退出了教学,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因此,现在全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还是要请一些职业设计师来授课,来促进知识的改变,因为在这种需要实践的项目里面,那种劳动,那种现场创造的过程,有时候就是知识的一部分。它不是完全靠文字和语言能够传递出来的,如果是一个完全系统化的理论体系,靠文字全部能替代的,那这个学科靠计算机就能被完全替代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看到的丰富多彩、星光灿烂,都是源于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因此,这种个体的认知,我觉得计算机和屏幕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这个声音被压扁了之后,被转译之后,变成物理性的频谱再被释放出来,它和面对面的交流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我很强烈。因此我现在的研究中,很少用二手资料,大概70%以上都是我自己得到的一手资料。如果我谈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还在世,我尽量会想法设法与他见面,同他交流。这也是今天比较优良的教育里面,指导者常常会问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是什么?独特性在哪里?
价值有时和独特与稀缺还是有密切关系的。
营造类的课程,这些年请职业设计师来讲授他们的创作经验,这些经验会对课堂理论进行修复。此外,我记得大概是十几年前开始吧,越来越多等比例的设计训练开始进入课堂,现在这种形式在中国也越来越多,尤其在建筑、环艺这些空间设计类专业。很多学校也在搞建造节,但是建造节的根本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中国学者太多的关注,这点比较遗憾。因为营造活动本身是与人类学层面的认知是有关系的,营造就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它要考虑人的本体,包括考虑做为对象的“物”,考虑现场。
2008年的时候,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有一个课程请我去评审(他们有一个项目要参加威尼斯的建筑双年展),观摩完他们的课程,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设计作业,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用了四个星期,现场建造用了八个星期。两个老师带着十二个学生在阿尔卑斯山上海拔大概三四千米的地方去搭建一个音乐节的舞台。这些构件都是在学校的参数化工房里完成的,但是为什么老师要跋山涉水,带着安全帽,调用直升机和载重卡车,像工人一样拿着锤子要把这个东西建出来?我觉得这是欧洲精英教育体系的觉醒,因为像营造这种体系,它是和劳动是有关系的。认知的途径除了思维与知识体系的推理之外,还需要靠身体。身体认知非常复杂,不可言说,它包括对物的感知,包括对劳动,对环境与场所的感知,它是一系列综合性的体验。所以像这些内容将来如何用网络授课去解决?我认为不能太乐观。


项目工程照片-日照科技馆
Q
2020届毕业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届,将是首次通过网络答辩获得学位的一届毕业生。您在这段时间内对毕业学生的指导工作是否会发生相应变化?您是如何应对的?
苏丹:
变化就是有些学生滞留在外地,有些学生还在北京。我要求在北京的学生是一定要见面(指导)的。现在我的三个硕士都已经完成了答辩,其中有一个硕士见面三四次,其他都是在网上指导。网上指导我认为可以控制大的理念、他的表述、他的论证,这些都问题不大,但是指导设计有很大的困难,在小小的屏幕界面上判断图纸信息是很难的,对图纸信息的某些内容进行讲述的话,在现场可能一个动作就可以表达清楚,但是在屏幕里要说半天。有时候遇到无法详述的障碍,语言中的冲突与激烈也会增强,然后再回过来和学生道个歉。在这个阶段,面对新生事物再加上疫情,大家都有一种本能的紧张感,所以大家在这个阶段会比较配合。但是当它(网络指导)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学生们还会这么配合吗?我是比较怀疑的。 目前对于本科生,我还在按一周看一次图纸做两次交流这种形式进行指导,学生之间个人能力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在教育上需要采取一个因材施教的方法,遇到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尽量让学生能有所进步,达到一个基准。能力强的学生要求也就会高一些,希望他能产生让我感到震惊的成果。这些年也有这样的学生,虽然不是被所有人认可,但我认为他的一些思维包括作业对我是有帮助的,教育里面还是有这样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不能自负。今天的教师 一定要理性地认知这个时代,认知自己,认知自己的教育对象。

项目工程照片-日照科技馆
Q
您认为此次授课指导等工作形式的被动转变是否是对未来教育范式的一种启示?
苏丹:
我觉得所有的创造与发展,都是基于危机的,这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所以通过目前这种形式,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些缺陷,但我相信恰恰是这种问题,能够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工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互联网技术会变得更加人性,更加真实。
另外这次疫情之后,我们一定还会面临很多其他不可预知的问题,所以这种全球化、流动以及对现场的感知一直会面临各种阻碍,我们会想用新的手段去辅佐、去解决。比如说对现场的理解,静态的图像是不够的,还要让它动起来,甚至要有一定的声音去刺激其他的感官,当然这种刺激还是和现场有区别,因为它是主观加进去的,如果说是注重现场的声场,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有一批实验性的电影是非常注重声场的,比如墨西哥电影《罗马》,我看完很感动。后来和一个音乐家朋友讨论该电影时,才了解到这部电影在当年研究声场,研究实验电子音乐方面是做的最好的。还有就是像张扬导演拍的《冈仁波齐》的姊妹篇《皮绳上的魂》,开始注重声音和声效,140分钟的电影,声音有113分钟,声场很特别,这个声场不是我们过去讲的那种旋律性的,而是真正那种物理性的,是风声,以及平常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如山峦上的声音、沙砾和水流动的声音,这便于我们对图像进行一种补充,是我们对环境的体验,对文化的认知有进一步的提高。
2007年,我在意大利米兰双年展设计博物馆看伦佐·皮亚诺的个展,那个展览是当时跟他合作做设计有二十年的一个设计师做的。在解释他的作品时,每件作品每一个构造节点的展现里都有配乐,而这种配乐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具有麻醉性的旋律性歌曲,它是那种表达劳动过程中关于机械建构过程中的环境声效,是我们无法听到的声谱,把这种声音释放出来就很有意思。我觉得过去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示范,所以我们塑造今天的形式也不一定是全新的创造,需要对过去有一种再认识、梳理和寻找,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项目工程照片-日照科技馆
隔离中的学术思考
Q
您策划的云展览“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馆“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成功开幕,开幕式上您提到”疫情终将过去,但记忆应当永存。“您希望这些作为记忆载体的展品能够向社会传递何种意义?
苏丹:
我们是一个比较健忘的民族,很多苦难过去后,大家不太愿意面对苦难的记忆而选择了遗忘。 但是人类的进步恰恰又是由苦难刺激后形成的反省,形成的自觉。艺术博物馆作为这样一个具有文化公信力的机构,有责任去给大家做个记忆的备份。在你即将遗忘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铺陈出来,让你回到那个时间状态下,警示你。在每一个当下的过程中,很多东西要及时保存,要不然的话,在将来所谓的“苦难”又会变成一个抽象概念,而抽象塑造出来的苦难陈述是很乏力的,完全没有质感。所以这个物证很重要,其中图像作为当下一种主要的记录和表达方式,它记录人的表情,社会的状态,环境的变化,它有很强大的反映客观事实的力量,超越传统的绘画或雕塑的方式。所以我们是出于历史的责任,把这些经由整个社会的记录做成档案。另外在展览中, 对作品的评价,艺术性不是第一位的,而视角的独特性、稀缺性才是第一位的,要从人的个体感知出发,看到这个时间段里空间的变化,因为时间和空间是最基本的存在。

Q
此次疫情使得人和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隔离也是特殊空间关系的一种,您认为在这种关系下,网络环境作为一种信息空间的窗口,它应如何与传统的实体空间平衡?
苏丹:
我们应该感恩这种技术的创造,能够在家中自我隔离,自觉配合,与网络的存在密不可分,与电视的存在密不可分。 人在被隔离的过程中,需要自己创造一个纵深感来打破物理的壁垒。阅读曾经是一种主要方式,过去文字给人一种抽象的延伸空间的可能。但是今天的东西很直接,比如电视挂在墙面上,告诉你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次有一个作品就是我一个朋友Maurizio Bortolotti拍摄的,他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策展人,曾经给重要的建筑理论家、评论家彼得·艾森曼做过展览。他这次作品由二十多张图片组成一个矩阵,拍的都是家里的电视,但电视里的画面都是意大利的场景。他说:“今天电视变成了我们看世界的窗口,但是我选择的画面都是意大利的画面,这意味着我在窗口之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思辨, 表达了自我意识中的空间意味。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讲,窗口带给我们很多信息,是我们在非常时期的行为佐证, 人们从这个窗口中得到信息并纠正自己的行为。

Q
您在疫情期间,是如何坚持推进学术研究工作的呢?
苏丹:
百感交集,它是全人类的一个灾难,但是对个体来讲,影响的差异性还是有的。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节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是挺难得的。在之前的许多时间里,我对2003年非典那段宅在家里的时间是怀念的,因为有时间去思考。今年从一月下旬到现在,我自己写的东西大概有十万字了,到三月底,我的文章已经写了有16篇了,我计划在两年以内再出一本书,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本小说,最近我快把结尾都写完了,原本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计划。这个时期就是因为社会和自己放慢了节奏,开始重新认识生活。天天在自己的房子里,开始进厨房了,开始洗衣服了,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正常人要面对的,但过去大家都像个商务人士一样要跑来跑去,这些事物对生活的个体来说可能都已经变得抽象了。很长时间里,我们这种人甚至说是没有生活,也不知是我们抛弃了生活,还是被生活抛弃。 当你没有生活的时候,你得到的所有的情感输出之后就是可以打动人的吗?未必。
知识不停地被贩卖,是需要被我们所警戒的,还是要回到地面的。在这个阶段,每天要多走路。管控严格期间,自己会像华子良一样绕着楼群不断转圈,最近能够出社区了,我就会走得更远,走动这个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很多东西。长时间没有这种习惯了,因为飞行的时候更多,我们都希望速度更快,但速度更快的时候实际上是空间消失的时候,地铁和飞机上都是没有空间的,社会性的空间是消失的,你看到的都是云端的景象。从物理空间回到社会空间,回到自己生活的社区的过程中,对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触动。 所以这时对自己输出的成果能有机会去慢慢打磨,内化的过程变精细了。

第22届米兰国际三年展中国馆“设计中的环境意识” 海报

第22届米兰国际三年展中国馆“设计中的环境意识” 现场照片
Q
您认为此次疫情所催生的产业格局与形势,会对环境艺术设计学科产生何种影响?
苏丹:
环境艺术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环境设计可能暂时变化不了。现在大家急于发声可能都是希望自己的专业和局势应对能产生关系,当然这次疫情是影响人类社会整体结构的,但有些学科的反应可能会在第二、第三阶段才出现。我想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艺术,反应会更激烈,会有更多我们积极代入的东西,但是这种思考和行动传递到环境设计领域,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某种程度上,火神山医院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过去的医疗建筑分类里很早就存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80年代还专门作为招收研究生的专业方向。 但是(疫情)对社会空间形态有何影响?我们会反思。比如说过去我们经常批评中国的大院,强调走向开放体系,比如海德堡大学就是一种典型,有校门没有校园,完全和城市融为一体。我过去有一个硕士学生一直研究“中国大院”的形态和文化背景,做了很多调研。他读博士时跟从德国资深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托马斯·赫尔佐格,在德国继续做对“中国大院 ”的研究。对大院形态的研究更多的时候是带有批判性的研究,但是这个时候你却发现,中国这次防控疫情的成功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大院文化;还有就是我们交易结算的方式避免了纸钞;再有就是东亚这种文化,大家比较容易响应集体号召。其中大院形态上的这种封闭性反而体现出便于管理的特点,所以对于这个形态的空间类型回过头来想,如果未来长期处于这种时断时续的管控状况,这种空间格局可能会变得更有价值。 这就是你重新判断过去你所批判的对象的开始,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之后,会改变对错的标准。

第22届米兰国际三年展中国馆“设计中的环境意识” 现场照片
危机下的设计责任
Q
在此次疫情的危机下,从视觉传达设计到服务设计,许多设计学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抗击疫情的运动,环境艺术作为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具备很强系统性的设计学科,应该以何种方式支持抗击疫情的运动?
苏丹:
环境艺术方面,艺术家可能会做一些行为、装置,让人们反思人和环境的关系。人的活动减少了,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评判人和环境关系的凭据, 说明人对环境的介入需要适度。
今年十月份在昆明会有一个法国人做的展览,叫“叶脉”,他发现区域内的植物有一定的社会性,会平均分配水源、互相传递信息,与我们传统对植物的判断完全不同。我觉得那些处在前端的学科领域,如环境、科学、艺术,其成果会纠正人的态度,影响人的行为规范,以及空间的形式 。所以我觉得当下环境设计不会马上做出对应,因为病毒主要是受制于宿主的流动,第一个层面的反应应该是与政策法规和文化习惯的调控变化,比如疫情会慢慢改变中国人的用餐方式,变为分餐制,当分餐制影响到生活道具设计的时候,这是第一环节。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会变,再往后可能厨房的格局会变,但距离影响到大的空间模式更迭还很远。 所以我觉得它的反应会相对滞后,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冷静与客观,不要武断地对未来进行潦草和仓促的断言。





窗口档案展
Q
从大的泛设计学科层面而言,您认为我们在应对诸如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时,应当担负起哪些社会责任?
苏丹:
设计就是媒介,能够把政策、技术领域发生的变革尽快转变到生活场景中,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并非研究最尖端技术的人,但技术成就也需要我们去分解、组合、打包,其实就是一种媒介的作用, 在媒介过程中实现一种温和的或华丽的转身。



《琴台琴》


2015年,舞剧《puzzle me》(谜)在意大利演出
总策划:苏丹

2015年,舞剧《puzzle me》(谜)在意大利演出,苏丹作为该剧总策划上台谢幕
图片提供/苏丹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采访撰稿/易昊天 工业设计系2017级硕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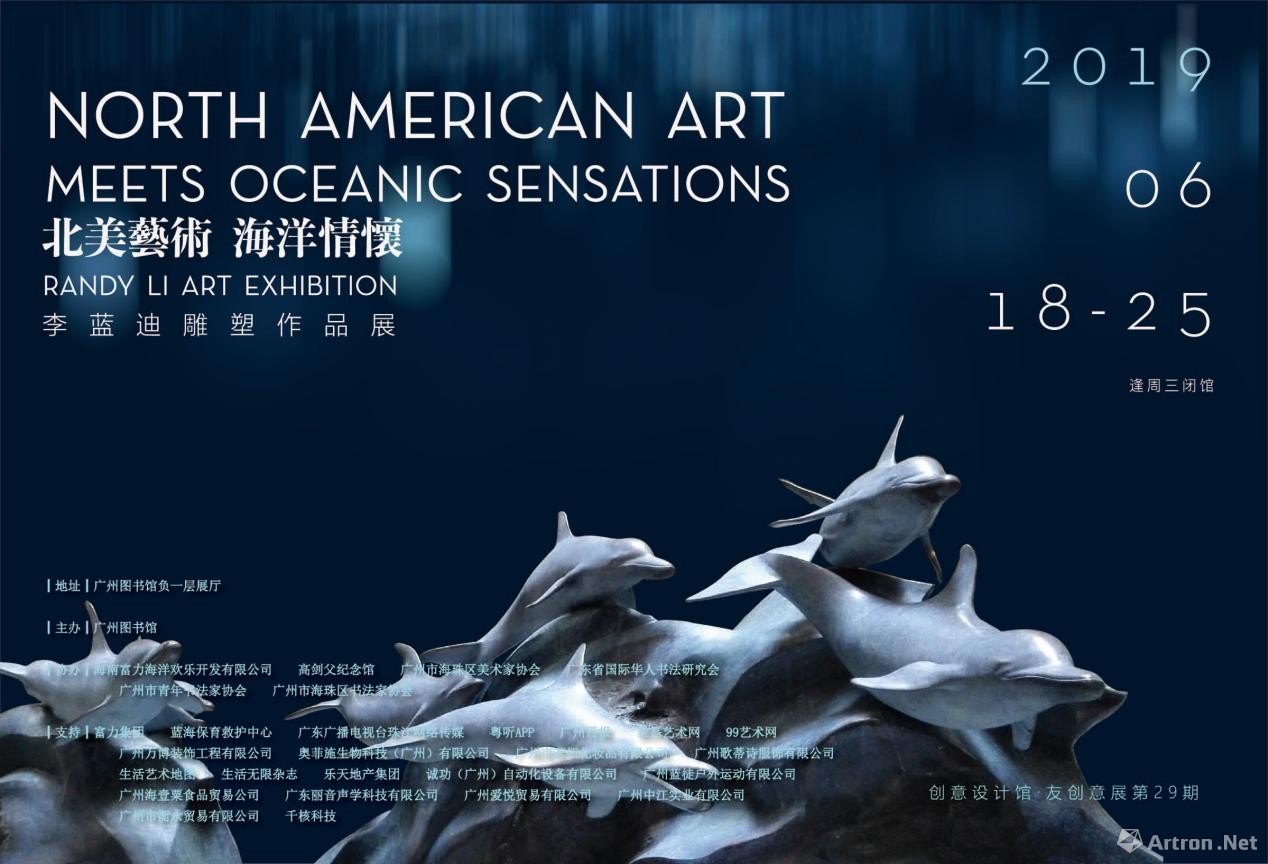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