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艺术家,论个人境遇,很难找出比苏轼更悲惨的。他所置身的时代,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等的尴尬与荒谬中,都与苏轼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语。苏轼的文字——像《寒食帖》,有尖锐的痛感,却没有怨气。
苏轼画像 赵孟頫
我不喜欢怨气重的人;具体地说,我不喜欢愤青,尤其是老愤青。年轻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物心怀激愤,还可以理解。但人到中年以后,仍对命运忿忿不平,就显得无聊、无趣,甚至无理了。
怨气重,不是在表明一个人的强大,而是在表明一个人的猥琐与虚弱。苏轼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气包,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倘如此,他就不是我们艺术史上的那个苏轼了。
他知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夜与昼、枯与荣、灭与生,是万物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因此,他决定笑纳生命中的所有阴晴悲欢、枯荣灭生。
他不会像屈原那样自恋,把自己当作香草、幽兰,只因自己的政治蓝图无法运行,就带着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投身冰冷的江水,纵身一跃的刹那也保持着华美的身段与造型,就像奥运会上的跳水运动员那样;他不会像魏晋名士那样装傻充愣,一副嬉皮士造型;也不会像诗仙李白那样“皇帝呼来不上船”,醉眼迷离爱谁谁,一旦不得志,随时可以挥手与朝廷说白白——要不他怎么叫李白呢。
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苏轼做到了;当然,是历经了痛苦与磨难之后,一点一点地脱胎换骨的。
木心说:“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木心:《文学回忆录》,第2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话有点随便了。实际上,豪放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在炼狱里炼出来的,既有文火慢熬,也有强烈而持久的击打。
苏轼的豪放气质,除了天性使然,更因为苦难与黑暗给了他一颗强大的内心,可以笑看大江东去、纵论世事古今。他豪放,因为他有底气,有强大的自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无论周公瑾、诸葛亮还是曹孟德,那么多的风云人物,那么多的历史烟云,都终被这东去的江水淘洗干净了。神马都是浮云,都是雪泥鸿爪——雪泥鸿爪这词,就是苏轼发明的。
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画墨竹(《潇湘竹石图》),画石头(《枯木怪石图》),都是要表达他心中的高贵。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他的心是宽阔的,所以他爱儒,爱道,也爱佛,最终把它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既不远离红尘,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他无论当多么小的官,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
灭蝗,抗洪,修苏堤,救孤儿……权力所及的事,他从不错过,他甚至写了《猪肉颂》,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横流的东坡肉。它的烹食要领是:五花肉的肉质瘦而不柴、肥而不腻,以肉层不脱落的部位为佳;用酒代替水烧肉,不但去除腥味,而且能使肉质酥软无比……
还是在黄州,每当日暮时分,他从东坡的农田荷锄回家,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轼都泰然自处,有时还跟着他们开玩笑。
在儋州——他的末日时光里,他还不忘调侃自己几句,说自己年纪大了,再也不能和小姑娘眉来眼去了。在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像海明威所说:对于一切厄运,都要“勇敢而有风度地忍受”。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年轻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枯木怪石图》
二
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多高,在上帝眼里,他终不过是一只蚂蚁。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深深地堕入凡尘,就像《寒食帖》里所写“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美艳的“花”转眼之间就会堕入泥土,但纵然是泥土,也有它的价值与尊严。他的生命,一头连着最凡俗、最卑微的生活,另一头却连着最深邃、精致、典雅的精神世界。
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那些身处华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灯青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轼……
词本是文人遣兴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如林语堂所说的,“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4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到了苏轼手里,才真正有了文学的气象,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第119—12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他的散文,超越了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拒绝了宫殿语法,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
他的书法,既不像唐代楷书那样强调法度、拘紧理性,也不像唐代草书那样叛逆、那样张牙舞爪,而是将自己的个性挥洒得那么酣畅淋漓、无拘无束。
苏轼 《人来得书帖》 纸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帖是苏轼写给友人陈慥(字季常)的书札,内容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表示慰问。行笔自然流畅,姿态横生,秀逸劲健,是苏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
苏轼最恨怀素、张旭,在诗里大骂他们:“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他追求历经世事风雨之后的那份从容淡定,喜欢平淡之下的暗流涌动,喜欢收束于简约中的那种张力。他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字,不是为纪念碑而写的,不见伟大的野心,却正因这份兴之所至、文心剔透而伟大。
他的绘画,传到今天的只有两幅:一幅叫《潇湘竹石图》,还有一幅叫《枯木怪石图》。但他倡导的文人画理论影响了金元明清,余绪至今未断。
苏轼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认为他们少文采、没学问,因而只知照猫画虎,不见风神与性情。文人画在两汉魏晋就有起源,但有了唐代王维,文学的气息才真正融入绘画中,纸上万物才活起来,与画家心气相通。至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轼手上,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辉煌绚丽的唐代艺术,到了他们手上,立即退去了华丽的光斑,变得素朴、简洁、典雅、庄重。后来的宋代画家把复杂多变的世界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绘画由俗世的艳丽遁入哲学式的深邃、空灵。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远不可能画出宋代水墨的丰富,因为墨汁里边掺了太多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游动。
苏轼带来了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观念革命,他因此成为北宋继苏惟演、欧阳修之后的第三位文坛领袖,成为中国艺术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大师,也成为我的心头最爱。
三
这份美,被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画在一幅图卷里。
这幅艺术史上的名画,记录了元祐二年(1087)五月,苏轼在“元祐更化”中返京,与朋友们在王诜的西园举行雅集的情况——王诜不仅是当朝驸马,也是著名画家(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皇家秘藏·铭心绝品——《石渠宝笈》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特展”,展出有王诜的名作《渔村小雪图》)。那次聚会,参加者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还有僧人圆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陈碧虚,共16人,加上侍姬、书童,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
李公麟 《西园雅集图》
《西园雅集图》几乎成了中国艺术家迷恋的经典题材,仅李公麟一人就画过团扇、手卷两种不同的本子。南宋马远,元代赵孟頫(传),明代仇英、陈洪绶,清代张翎等著名画家,也都画过同题作品;其中,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卷现被私人收藏,马远《西园雅集图》长卷收藏在美国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赵孟頫《西园雅集图》卷和仇英的《西园雅集图》轴分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之(养心殿)第二册中,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中的场面让我想起文艺复兴画家拉斐尔(Raphael Santi)为教皇宫殿绘制的大型壁画《雅典学院》——一幅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主题的大型绘画,在这幅画上,汇集着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语法大师伊壁鸠鲁、几何学家欧几里德(一说是阿基米德)、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哲学家芝诺……画家试图通过这样一场集会把欧洲历史的黄金时代永久定格。
《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
那一份光荣,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的雅典学院。
美丰仪,成为当下时兴的一个热词。但真正的美丰仪,不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萧景琰,而是真实历史中的苏轼、苏辙、秦观、米芾。他们不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
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见史泰隆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艺术与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仇英(传)《西园雅集图》
四
苏轼生活的时代,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他一生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位皇帝,一茬不如一茬。
叶嘉莹说:“北宋弱始自仁宗。”(叶嘉莹:《古典诗词讲演集》,第2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宋仁宗当年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对苏轼器重有加;宋英宗性久慕苏轼文名,曾打算任命苏轼为翰林,因为受到宰相韩琦的阻挠,才没能实现;宋神宗也器重苏轼,却抵不过朝廷群臣的构陷而将苏轼下狱,纵然他寄望于苏轼,也犯不着为苏轼一人得罪群臣;宋哲宗贪恋女色,十四岁就想着以宫中寻找乳婢的名义给自己找女人;宋徽宗玩物玩女人,终致亡国,关于他的故事,留在后面细说。公元1101年,苏轼死在常州,距离北宋王朝的覆灭,只有25年。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快乐与凄凉,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艺术里。
在悲剧性的命运里,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开岭所写的:“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王开岭:《夜泊笔记》,见《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集》,第1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我经常说,现实中的所有问题与困境都有可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许多人并不相信,在这里,苏轼就成为从现实围困中拔地而起的一个最真实的例子。时代给他设定的困境与灾难,比我们今天面对的要复杂得多。苏轼置身在一个称得上坏的时代,却并不去幻想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时代里也会有不好的东西。
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因此,苏轼没有怨恨过他的时代,甚至连抱怨都没有。这是因为他用不着抱怨——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样的时代,更不会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做出精心的设计与谋划。
有的艺术家必须依托一个好的时代才能生长,就像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感叹的:他生得太早,或者太晚了。但像苏轼这样的人是大于时代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时代都压不死他。
他给予那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
木心说,艺术家仅次于上帝。(木心:《文学回忆录》,上册,第4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寒食帖》
元丰七年(1084),也就是苏轼写下《寒食帖》之后的第三个春天里,宋神宗把苏轼调任到离汴京不远的汝州(今河南临汝)。他从黄州出发,顺江而下,过金陵时,他一定要去拜见一下已经辞官、在金陵城与钟山之间的半山园隐居八九年的王安石。闻听苏轼过金陵,王安石等不到苏轼前来晋谒,就已骑上小驴,去江边船上,主动去寻找苏轼了。因为作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关注着远在黄州的苏轼。苏轼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让王安石深感着迷。艺术在不知不觉中,弥合着二人在政治上的巨大鸿沟。相别时,王安石发出这样的长叹: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不幸言中了。
像苏轼这样仅次于上帝的人,在历史中果然成了绝版,徒留我们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时代里,发出千年一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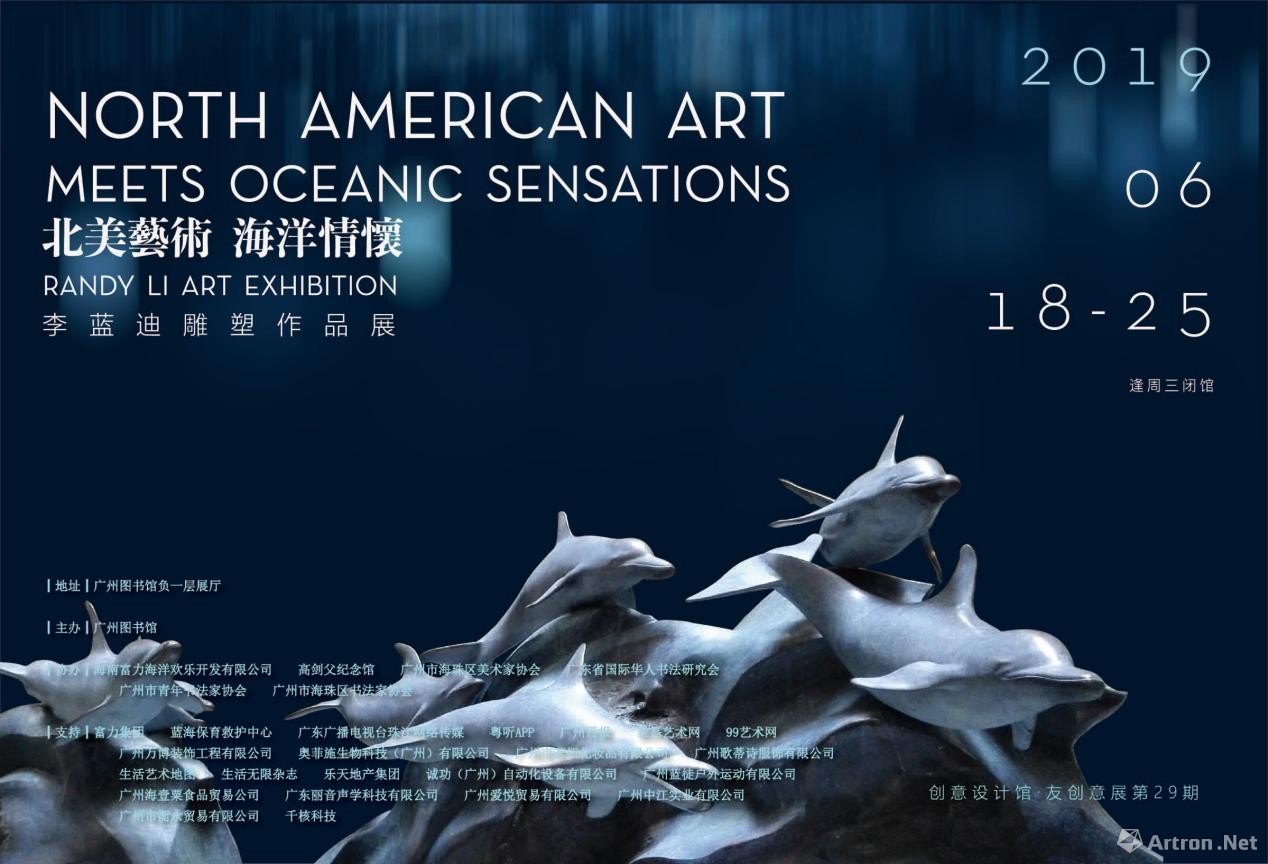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