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随手拿一本《吴昌硕信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其中都是吴昌硕写给顾麟士的信。除去吴氏行书与信中内容,令我大开眼界的反而是缶翁所用之信笺,图样或砖文或花卉,为其书法增添了古意。
设想写信的与看信的双方都为“话旧”,其含义之切,印于笺上,真是神来之笔。我随即裁一小纸,临摹一张,若挂在茶室书斋,想必也恰如其分。
吴昌硕致顾麟士手札
张大千过生日,作画赠挚友
隔了没几天,我读董桥《克雷莫纳的月光》(牛津出版社,2013),开头就是一篇《话旧图》,当中提到,一九五三年初夏,张大千(1899—1983)致信朱省斋(1901—1970),告知自己即将从南美到东京,希望能够在东京与朱会晤,朱随即从港赴日。是年农历四月初一,正是大千生日,朱省斋请张大千在东京上野万寿楼吃面,分别后,张作《不忍话旧图》赠朱。
董桥《克雷莫纳的月光》封面
张大千《不忍话旧图》
朱省斋,本名朱朴,字朴之,号朴园,晚年移居香港时改名朱省斋。朱省斋是张大千离国后在港结识的挚友。朱氏外舅即汪伪政权之红人梁鸿志(1882—1946),梁氏收藏古代书画甚富,其收藏三十三件宋人手迹(后入藏故宫博物院),号称“三十三宋斋”。张大千所藏黄庭坚《经伏波神祠诗卷》、苏轼《书维摩诘赞卷》等名件均经过朱氏介绍而来。
(左)张大千、(右)朱省斋
黄庭坚《经伏波神祠诗卷》
一幅《不忍话旧图》勾起“话旧”
之前我见吴缶翁信笺上有“话旧”二字,今又见大千画《不忍话旧图》,这一来一去,“不忍”二字令人揪心,值得玩味。我停下了阅读,思索“话旧”与“不忍话旧”之不同意境,犹如回味一枚橄榄,又如同思索一句新腔。
张大千于《不忍话旧图》上题跋“省斋道兄知余将自南美来游东京,遂从香港先来迎候,情意殷拳,倾吐肺腑,而各似人事牵率,未得久聚。治乱无常,流离未已,把臂入林,知复何日耶?为写数笔,留以为念,传之后世,或将比之颜平原明远帖,知吾二人相契之深且厚也。癸巳四月同在东京不忍池上,蜀郡张大千爰”。其中提到的颜真卿《明远帖》是颜写给蔡明远的一封信,记叙了蔡对颜真卿的追慕之心,颜遂有此书。清人王虚舟评价此帖“此鲁公作人坚刚如铁,乃于朋友之间万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看完题跋,方知“不忍”二字内涵。1956年溥儒到朱氏东京寓所见此图,遂题“相逢离乱后,林下散忧襟。共作风尘客,同怀云水心。与生元亮酒,情契伯牙琴。话旧传千古,宁知鬓雪侵。丙申春二月同客江户,溥儒。”
朱省斋《朴园日记》封面
2017年盛夏,我与内子同赴东京国立博物馆看画,该馆即位于东京上野。上野公园类似一座小山丘,这是我第二次去,由于东京错综复杂的地铁与JR线,我这次坐错了站,或走错了出口。我走到了山丘的另一面,天热人急,我始终找不到博物馆的影子。烈日下见一池塘,其中开满了荷花,花蕊之大、荷叶之盛,令人惊叹,其中还有栈道使人徜徉。我看到了铭牌“不忍池”。
回沪后我一听见朋友要去东京就推荐他们去不忍池,并说比西湖的荷花更胜。因为西湖大不可能种遍荷花,而不忍池小,种满荷花,反而雄健。
东京上野不忍池一角
读书读到张大千有《不忍话旧图》,想起自己于东京不忍池所见,即有共鸣,所好奇的是不忍池边还有无万寿楼,若仍在,定当登楼,果腹是其次,最好也有画家契友话旧,归后我也能得一张《不忍话旧图》补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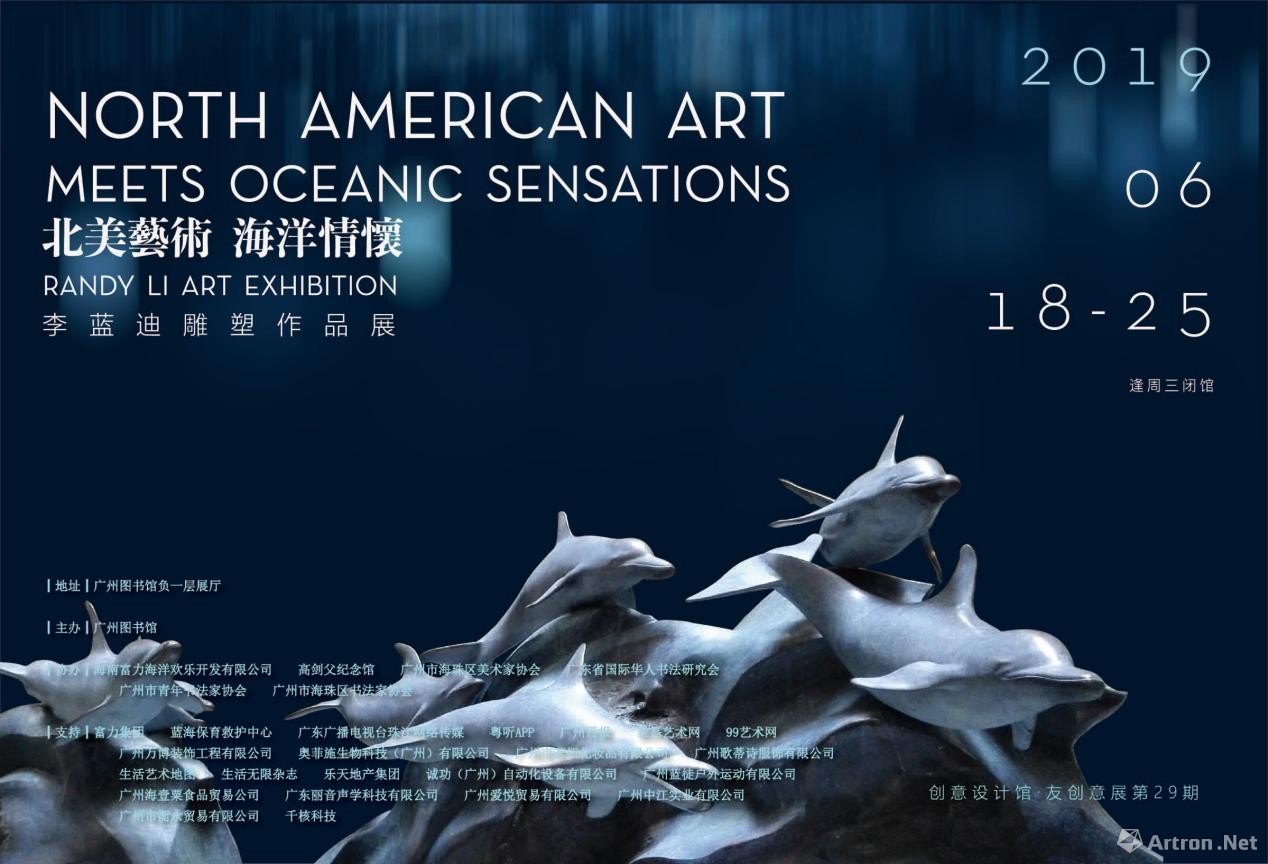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