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渭 墨花图(局部) 卷 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1521-1593)出生于明代中后期,他生前虽谋略出众,尤其“好奇计,谈兵多中”,但终究“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去世多年后,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发现了这位奇人,写奇文《徐文长传》,徐渭的声名才得以大显于世。在《徐文长传》中,袁宏道就预测徐渭以诗文为主的艺术作品“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确如袁氏所言,在“百世而下”的清中期,徐渭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其作品被当时的文士阶层所青睐。那么,这些文士阶层是如何赏玩徐渭作品的?赏玩方式跟今人相比有何不同?
丨赏玩的几种方式丨
雅集吟咏
清中期乾嘉盛世,社会稳定,文士阶层流行各种主题形式的雅集。在京师,每逢花开花落、立夏立秋、中秋重阳,诗文酒会几无虚日。就算在平日,文士之间也多有相聚。雅集的内容,以写诗论画最为多见。徐渭的一枚竹质印章,就曾出现在汪启淑举办的雅集上,作为吟咏的对象。
汪启淑是当时著名的藏印家,自号“印癖先生”——其辑录的《飞鸿堂印谱》至今仍是篆刻界赫赫有名的集名家印存之最者。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的一天,在工部任职的汪启淑邀翁方纲、朱筠、程晋芳、张埙、顾宗泰及蒋香泾一行集于其住宅“蜗寄轩”,诸人分韵吟咏汪氏所藏古印。其中,翁方纲分得李清照玉印,朱筠分得李广铜印,程晋芳分得李纲瓷印,张埙分得徐渭竹印,顾宗泰分得李长蘅石印,蒋香泾分得徐石麒晶印,汪启淑分得赵孟頫夫人管道升牙印。分得徐渭印的张埙作诗《同翁覃溪、朱笥河二学士、程鱼门吏部、顾星桥舍人、蒋香泾进士,集汪秀峰工部蜗寄轩,分咏古印,得徐渭竹印》一首,此诗载于其著作《竹叶庵文集》。
需要说明,汪启淑这次雅集的主题是让宾客赏鉴他所藏的名人古印,进而再分韵吟咏,这两个环节共同构成这次雅集的内容,“吟咏”与“题诗”虽形式相近,但性质不同,应予区分。
画作题跋
对一幅书画作品作题跋诗,是传统中国文士钟爱的赏玩方式,宋代苏轼名诗《题惠崇〈春江晚景〉》就是此类。清中期诗文活动繁盛,我们选取有关徐渭题跋诗的两个代表性诗人案例。
黄仲则是清中期诗坛的天才诗人,是北宋黄庭坚弟黄叔达之后,与洪亮吉并称“洪黄”。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赴京候铨期间,他看到了一幅明代的《蕉阴宫女图》。想必徐渭擅画芭蕉已在当时被人熟知,所以黄仲则在作题跋诗时,随即想起徐渭,并选取徐渭芭蕉图中作诗的一韵,以次韵的形式作了《题明人画蕉阴宫女即次徐文长题诗韵》:记调弦索侍深宫,手种芭蕉绿几丛。行过蕉阴却回顾,美人心事怕秋风。(黄仲则《两当轩集》卷十五)
作为乾嘉诗坛领袖,翁方纲相较其他乾嘉学者,他的诗文中徐渭次数出现较多,其中题跋诗有《徐天池水墨写生卷》《徐天池写生卷》《徐天池梅花》《徐天池墨荷》《徐文长墨荷二首》等,载于其著作《复初斋诗文集》。
临摹仿拟
临摹徐渭作品的清中期文士阶层不止是职业书画家,很多有官职的文人或学者也参与其中,作为闲暇时的怡情雅事。
李秉绶是乾嘉道时期著名的书画家,早年曾在京师任职工部都水司官职,后嫌公务缠身,壮年时即辞去官职,定居桂林,专心画事,成为“岭南画派”的肇始人。李秉绶的画,其写意风格主要取法自白阳青藤一路,《粤西先哲书画集序》载:“李秉绶,江西临川人……工书画,梅竹尤佳。写意花卉以沈周、陈淳为宗,旁及徐渭、华喦。兰石则专师钱载。”
张问陶(号船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性灵派诗文家,被公认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而他被诗名所掩的另一身份是书画家,且书画水平很高。《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张船山先生事略》载:“幼有异禀,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书法险劲,画近徐青藤,不经意处,皆有天趣。”从留存至今的张问陶书画作品来看,确有不少是走了徐渭的路子,如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西崖诗意图册之积水潭》。
流转交换
有两例涉及用徐渭作品交换他人作品的情况。
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库全书》纂修官、进士陈崇本购得一幅徐渭书法对联,联曰:“腹中饥冷磨难熬,头上霜浓晒不消。”友人张埙看到后特别喜欢。由于张埙藏有明代董其昌书法得意之笔《七律卷》,故陈崇本提出,欲以徐书和董卷相交换。面对这个要求,张埙很为难,但最终决定不交换,而是委托翁方纲临摹这幅徐渭书作。充满戏剧性的是,翁方纲在临摹时发现,此书是徐渭赝品。
曾任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一代文宗阮元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得到一幅徐渭旧藏《〈鹅群帖〉卷首画》,上有徐渭题跋。阮元的这件收藏品被作为友人的书画篆刻家黄易(号小松)看中,阮元便委托黄易把此画临摹于一砚台背面,并许诺对方,若能摹成,便以此画相赠。过了十天左右,黄易果然摹成,阮元跋《鹅群砚》记录此事:“元得徐天池所藏《〈鹅群帖〉卷首画》,鹅意态逼真。小松司马见而爱之。元曰:‘能摹砚背则奉赠。’越日果持此砚来,其神采出天池上。盖天池所能小松能之,小松之能天池所不能耳。甲寅冬阮元识于小沧浪。”由此看出,阮元非常满意黄易此刻。
赏玩鉴定
徐渭作品在清中期即已出现赝品,故鉴定成了赏玩徐渭作品的方式之一。清中期的金石书画鉴定领域,大学士翁方纲当属第一名家,平生过眼书画之多很难有人企及,此亦可解释为何上文所述的徐渭作品题跋诗中他所作的数量较多。
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五日,经学大儒毕以珣(号恬溪)携来一批古画求翁方纲鉴定,这些画有:沈周《桐阴高士图》、王翬《山水》、无款《芦雁》、文从简《梅石图》、徐渭《写生册》、虞楷《醉仙花》、陈洪《扇册》二十幅、沈周《松卷》、陈淳《写生册》等,经鉴定,徐渭《写生册》非真迹。
附带举一件徐渭的收藏品。乾隆四十二年(1777),金石书画家张燕昌(号芑堂)给翁方纲寄去一件明代万历元年出土的西晋太康年间瓦券拓本,翁方纲鉴定后认为,此瓦在明代出土后即被徐渭所收藏,并指出当时徐渭还为此写过诗。鉴定出来后,翁方纲作诗《张芑堂以晋太康瓦券拓本见寄,即徐天池赋诗者》。经查《徐文长文集》,确有此瓦券及徐渭作诗的记载:“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间冢中杯及瓦劵来易余手绘二首。劵文云……二物在会稽倪光简冡地中,于万历元年掘得之……”。可见,冢中杯及瓦劵是柳元谷用来换取徐渭画作的交易品。
刻碑捶拓
乾嘉两朝是金石学大盛的年代,该时期的学者们多以寄情山川寻碑、拓碑为平生快意事。被誉为乾嘉朴学“开国元勋”与“领袖”的清代大学者朱筠(号笥河)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浙江衢州游烂柯山时,专门嘱咐门人陈宋赋去拓山中所藏的唐宋碑刻及明徐渭断碑。
我们在其著作《笥河学士诗集》卷二十七《游烂柯仙洞》中看到,他在诗中交代了拓碑的原由,即“恐石漫灭”,这已经远超一般人仅因“嗜古”而拓碑的理念,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文物保护行为。
丨古今赏玩方式对比丨
上文所论的几种清人赏玩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赏玩高雅艺术品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的赏玩方式跟前代相比,有何变化呢?
最本质的是赏玩性质的变化。徐渭作品在今天已大多属于公立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国有资产,流散于民间的数量不多。这就使得赏玩性质从封建社会中的少众私人活动变成了政府认可、相关机构策划实施的大众群体活动,由此促成的赏玩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展览”。通过展览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有二:一是观众的数量急剧增多;二是观众的阶级性淡化。徐渭作品的观众已不是以往仅以文士阶层为主的赏玩人群,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观赏的机会,传统优秀作品真正变成大众的了。由展览为主的赏玩方式还衍生出各类其他赏玩方式,如各类文创产品或用电子技术虚拟现实的VR(VirtualReality)视觉体验,将来当然还会有更多的赏玩方式诞生。
深而思之,当今展览化的赏玩方式,其实是一种比较的方式。一场主题性展览上,往往会有画家各时期的若干作品出现,我们面对这样的展览,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比较各时期不同作品时,看到一个画家艺术探索的历程和最终风格的形成。之所以出现这种前人所未有的全新体验,还要归根于我们的时代。
采取以清中期文士阶层赏玩徐渭作品的视角,我们看到这些赏玩方式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传播方式,通过雅集、题诗、临摹、交换、鉴定和拓碑等方式,徐渭的形象和影响就这样在百年之后鲜活地展示出来。徐渭的作品不仅有书画和诗文,还有印章和碑刻。清中期文士阶层对徐渭作品的热爱是发乎于心、现乎于行的。比如翁方纲,在诗歌方面《方纲仿徐天池笔意作诗,次韵二首》《青藤书屋歌,为山阴陈九岩赋》,书法方面《缩临徐天池诗于两峰〈萧翼赚兰亭图〉后,即次其韵》,此外在其交游中还出现了一幅《徐文长像》,笔者曾另撰文探讨此类肖像画,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把所绘人物视作先贤来祭拜。如果把徐渭故居——青藤书屋——也算一件徐渭参与设计(徐渭至少进行过植青藤、书牌匾等行为)的“作品”的话,那么清中期文士还有更高一级的“玩”法,显示出他们对青藤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乾隆五十八年(1791),一个名叫陈永年的徐渭同乡“粉丝”买下了青藤书屋,之后此人及其子侄们对其进行修缮,并对之前陈洪绶所题青藤书屋之牌匾来了一个“修旧如旧”的保护,最后聘请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撰写《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旋由钱泳书丹,勒石立于青藤书屋。从记中得知,阮元还提议对方最好对徐渭墓地进行修缮,最后陈氏家族遵照了这一嘱咐。陈氏家族终于突破了“古不修墓”这一地方传统风俗障碍,在阮元鼓励下坚持对徐渭墓进行修缮,并形成每年春秋祭扫的惯例。阮元与陈昌的题记石刻,今嵌在青藤书屋的西壁上,它们是代表整个清人赏玩徐渭作品方式的最好注脚。
包子捷(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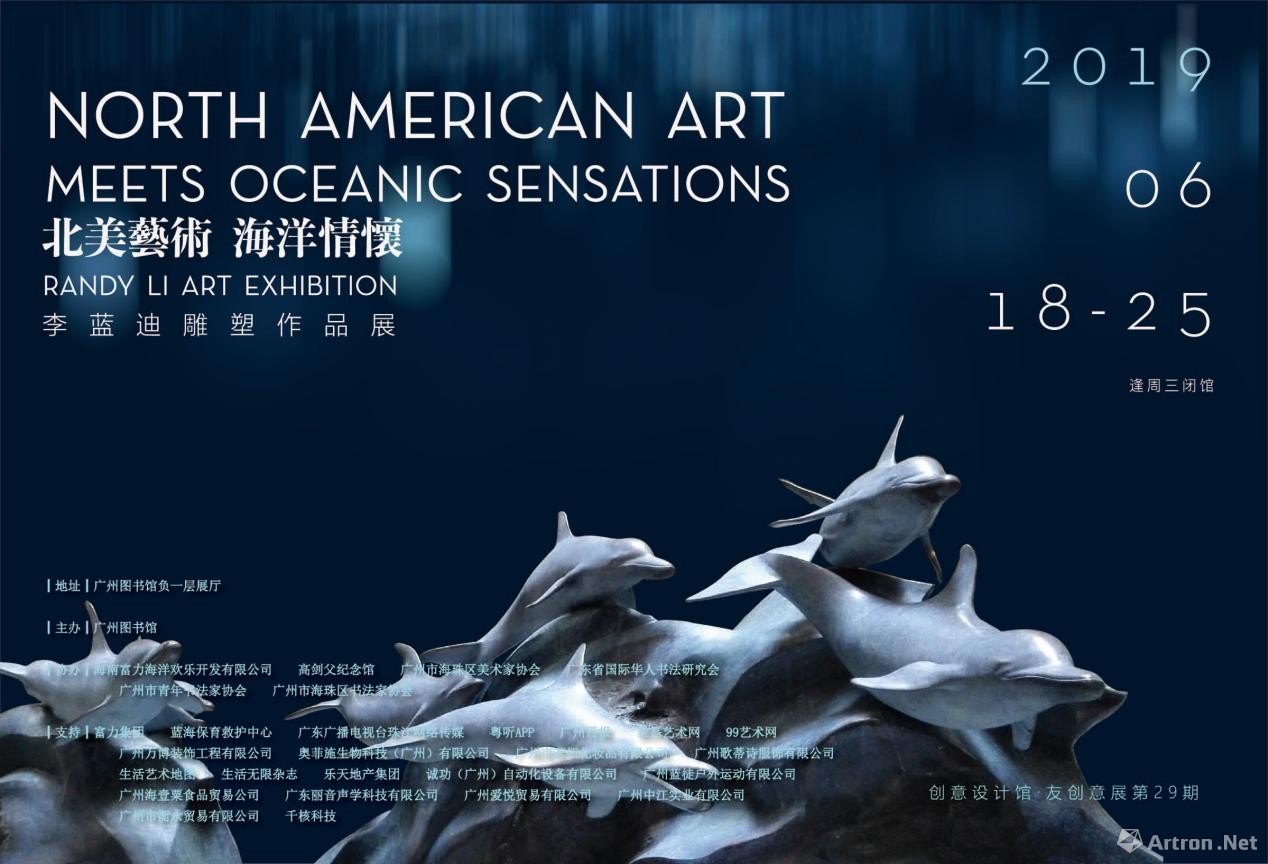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